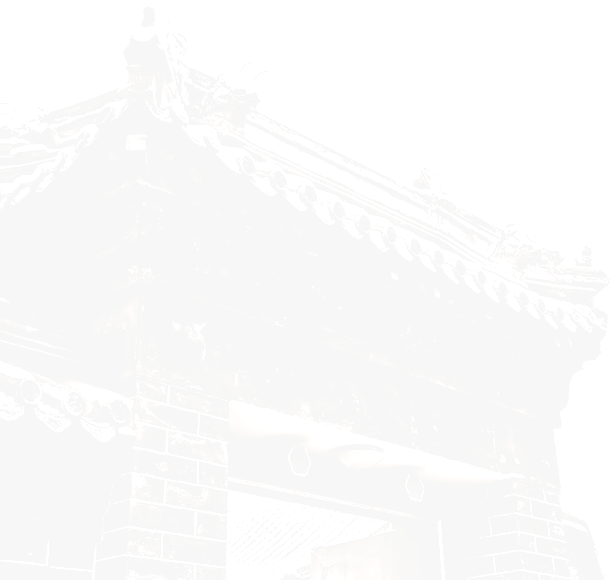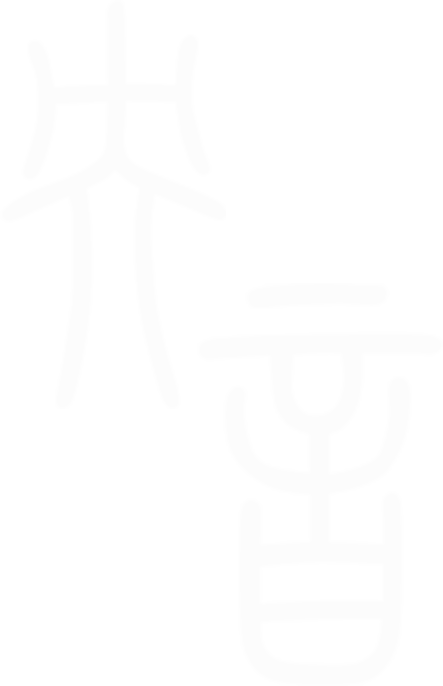2025年5月30日,在音乐学系党总支书记吴晓萍老师和中国传统音乐教研室张春蕾老师的带领下,音乐学系30余人于“艺术实践周”期间赴智化寺开展田野采风活动。
上午九时许,我们叩响了智化寺右旁的朱红漆侧门。门轴老旧,“吱呀”一声先遣,方听“咣”的一声响,厚重门板应声而开。众人鱼贯而入,霎时间眼前光影迷离,周遭空气亦随之一肃,历史的纵深感扑面而来。

智化寺前门
一、古刹偏安藏巷陌,赑屃独卧记荣枯
智化寺,这名号听着便有几分禅意,其始建可追溯至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这寺庙,委实会“藏”。初来乍到时,站在禄米仓胡同口往里张望,只瞧见寻常巷陌——谁能想到,这院墙之后,竟是殿阁连绵,藻井炫目,万佛庄严,一派煌煌大明气度!
下几步台阶,步入智化寺内。环看四周,钟鼓二楼,红墙黑瓦,在大殿两侧巍巍耸立;殿前,如此规格的古刹,照例有赑屃悠悠地趴着,背上驮着石碑,石碑顶端雕着盘龙,往下刻录智化寺的建寺历史。这座古刹被呵护得很好:黑琉璃瓦歇山顶,檐角蹲兽,斗拱层叠,连同下方朱漆门窗,在日光下熠熠生辉,几无岁月尘埃。只有赑屃石雕上的坑坑洼洼,证明了寺院确实久经风雨。正想进一步细观,却被通知大家集合了,于是,我们聚拢在智化门右侧,听智化寺京音乐管理负责人王娅蕊老师细说从头。


同学们一起聆听王娅蕊老师讲解智化寺历史
原来,此寺的“总包工头兼甲方”,乃是明代那位权倾朝野的大太监——王振。这位王公公,早年曾是明英宗朱祁镇的东宫旧侍,英宗即位,他自然是平步青云,一时风头无两。仗着圣眷优渥,又打着“感念皇恩”的旗号,这座私庙竟得英宗亲赐“报恩智化禅寺”之名,香火鼎盛,自不必说。只是花无百日红,到了清乾隆七年(1742年),王振的塑像被朝廷一纸诏令给毁了,寺院也随之由盛转衰。待到光绪年间,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殿宇颓败,不忍卒睹。1961年,智化寺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屡加修缮。1992年,成为“北京市文博交流馆”,至此,智化寺方才重开山门,广迎八方来客。
二、藏佛殿内观塑像,智化殿前听古音
听罢前尘旧事,我们鱼贯入内,向后院继续“寻宝”。此行的重头戏,不仅在于目观,更在于耳闻与心悟——那便是名扬海内的智化寺京音乐。

藏殿牌匾
先至藏殿。殿中那座体量惊人的转轮藏,无疑是视觉的焦点。好一座八面玲珑的木构宝塔!其势参天,昂然矗立,顶部更是坐着一尊毗卢遮那佛像,几欲捅破殿顶那片绘满卷云纹和莲瓣的藻井。细观其上,从顶部的金翅鸟、龙女、摩羯鱼,到转角力士的虬结筋肉、瞋目叱咤,再到三百六十五格屉面所雕佛像,乃至角柱上层叠的狮、狮羊、菩萨,无不精雕细琢,繁复至极。

藏殿转轮藏顶部毗卢遮那佛像与藻井
出藏殿,转入如来殿。这殿,比藏殿更恢弘。三尊大佛稳坐中央,胁侍两侧的大梵天与帝释天,慈眉善目,含笑而立;居中的释迦牟尼佛则端坐莲台,目光直视前方,透着一股洞察世事的超脱与神秘。其衣纹皆洗练流动,木质的质地,却如丝绸般顺滑。衣袍之上,沥粉贴金,龙、凤、狮子、麒麟等祥瑞附于其中。再放眼整座大殿,四壁上佛龛密布,如蜂房蚁穴,每个龛中都供奉着一尊小巧的漆金佛像,据说总数达九千余尊,直看得人眼花缭乱。这九千余尊小佛,与三尊主佛,或微笑,或垂眉,神态万千,共同营造出一种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立于殿前,两侧胁侍、后壁佛龛的目光,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唯有正中的释迦佛,依旧淡然出尘,以其洞悉而漠然的眼神,穿透重重殿宇,望向遥不可及的远方。

如来殿内右侧肋侍
这如来殿内万佛奔涌、宝相庄严,与此前在藏殿所见的转轮藏,在美学上可谓异曲同工,共同将一种“满”与“繁”的视觉冲击力推向了极致。中国传统审美,尤在水墨丹青、文人雅趣之中,常以“留白”为上,讲究“疏可走马”,以求“虚实相生”的意境。智化寺的雕塑美学,却悍然展现了传统美学谱系中的另一极——“密不透风”的繁复与铺陈。目之所及,几难觅半寸闲空,满眼皆是密匝的符印图腾、饱满到近乎溢出的线条、层层叠叠的构图叙事,共同织就出一派喧腾欢闹、几欲破壁而出的天界胜景。
放眼人类文明的长河,以“满”与“繁”来彰显崇高,亦非东方佛教之独擅。很多文明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艺术创作,都借助一种近乎饱和的感官冲击,来具象化对“无限”与“神圣”的向往。譬如,古埃及神庙壁画铺天盖地的象形秘语,欧洲巴洛克教堂几欲吞噬观者的涡卷与金箔,乃至南亚次大陆石窟造像生生不息的万神谱系,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极尽繁盛”作为通往神圣体验的路径之一——人类似乎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要将此岸可见可触的万般华彩,层层叠叠,倾其所有,去叩问那无形无垠之境的边缘。而智化寺雕塑的“满”的风格,也许是对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楼台,八功德水,黄金铺地,天乐鸣空”的具象化描摹,以排山倒海的冲击力摄受人心,令众生起欣羡皈依之念;也许是因为佛教中“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观念,只有如此繁密的图像才能勉强象征一二。

藏殿转轮藏一角
是耶?非耶?其背后真实的观念驱动,笔者也无从考证。有意思的是,智化寺既名“禅寺”,其美学与禅宗所追求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素价值观,却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本身就耐人寻味,或许这是明代“诸宗融合”趋势下,禅亦难免世俗与贵族化的一抹侧影?又或许,这里面掺杂了王振与英宗借此彰显煊赫权势、祈求现世福报乃至暗中聚敛财富的私心考量?凡此种种,委实难思难想。
然,于我等音乐学子而言,智化寺真正的“活文物”,并非这木石金漆的辉煌造像,而是正由传承人老师们精心呵护着的京音乐。乐者,天地之和也。早至轴心时代,东方、古印度及古希腊的先贤们,皆洞见音乐强大的感性感染力,并寄望其协和天地人伦。佛教传入中土,其梵呗的唱诵亦迅速与本土音乐文化相融合,智化寺京音乐便是这千年交响中的一脉遗珍。相传其源自明代宫廷音乐,后“下放”寺庙,成为佛事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智化殿正门
在智化殿内,我们见到了几位须发微霜,然精神矍铄的非遗传承人老师。他们头冠黑帽,身穿白褂,气定神闲,仿佛不是来表演,而是如常练功。
少顷,乐声起。乐队编制不大,却件件是“角儿”:一人持管子,此物源自古龟兹,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其音色苍凉,极具穿透力与金属质的苍劲,是乐曲的灵魂主奏;一人吹竹笛,以流畅的花音和装饰穿插于旋律中。左旁有云锣十面,音色清脆,在旋律线上方八度点缀,起到“提亮”的效果;右旁有鼓,声沉势雄,根据乐曲板式变化,构成乐曲的“板眼”框架;更有两只笙,间刻不停,持续吹奏出多音和声,为旋律铺垫出音响声场。与西方管弦乐团追求各声部融合、以和声功能为驱动的音乐语言不同,智化寺京音乐更接近一种支声的织体。即,各个乐器在演奏同一条核心旋律时,根据约定俗成的加花习惯,进行富有个性的润饰,繁简相让,和而不同。

智化寺京音乐27代传人
先是一首《小华严》开场,乐声悠扬典雅,仿佛置身于明代宫廷中。其“散、慢、中、快、散”的曲式结构,通过“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层层铺展、而后又万川归海般回归宁静。
一曲罢了,开始学习京音乐的入门曲目之一——《喜秋风》,照例是先学唱谱,再欣赏演奏;其后,又是一首意境幽远的《清江引》,亦是依循先唱后奏的规则。那旋律,古朴苍劲,自有其独特的“骨力”。
在学习唱谱的时候,我们亦步亦趋,努力模仿着那独特的发音与腔调。初时,口舌不听使唤,唱出来的调子南腔北调,不禁忍俊不禁。然渐渐地,随着反复练习,竟也咂摸出几分味道。韵唱过程中,为使旋律更圆活连贯,常在某些谱字之后缀上一个轻巧的“的”(阿口衬字,音di)字作为倚音或连接音;而一句唱罢,收尾时又往往要微妙地带出一个“呃”的尾韵。这些口传心授的细节,谱面上未必能一一详录,全凭师徒间的耳提面命与心领神会。

师生学习唱诵《清江引》
更深一层探究,这工尺谱及其唱诵、演奏实践,反映了一种与西方古典音乐截然不同的音乐观。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统中,乐谱往往被视为作曲家意志的载体,追求的是对作品文本的精确再现。然而,在工尺谱的体系里,音乐更多地存在于流动的实践之中。这种记谱与传承方式,也决定了其音乐在保持旋律骨架的同时,必然会随着时代、地域、乐师个人风格乃至方言习惯的不同而呈现出丰富的变体——譬如老师在教唱《清江引》时便提及,同一谱字,北京与河北的乐师,韵唱时会有细微出入;年事已高的师父,受其身体条件影响,也会选择省略某些谱字。这种“活态”韵唱与演奏的传统,与西方古典音乐“一音不改”的演奏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京音乐传承人与师生交流
与传承人的交流,更把我们从乐谱的学习引向了对音乐背后“人”的理解。胡庆学老师提到张振涛曾总结说,“韵唱是把三五个谱字,唱成十几个谱字,而演奏中则可达到上百个谱字”,当演奏者首先通过自己的嗓音去“体认”乐谱,去感受每一句的呼吸、每一段的气韵,这种内化的过程,使得乐谱成为演奏者身体记忆的一部分。所谓“口传心授”“谱简声繁”,或许正是此意。

吴晓萍老师与学生交流
末了,吴晓萍老师提到采风的重要性:“亲身感受和网上感受,那是天差地别!”的确,网络可以无限复制乐谱、音像,却无法复制特定历史场域所氤氲的独特语境;无法替代乐器与特定殿堂空间之间产生的微妙声学共鸣;更无法传递传承人现场演绎时那股子精气神,以及学习者与传授者之间面对面交流时,那份眼神、体态、乃至共同呼吸所交织成的温度。身体的“在场性”是构成完整、深刻经验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有些东西,非得身处此时此地,用全部的感官去拥抱,用敬畏的心去倾听,方能真正有所体会与感悟。这或许便是田野采风于人文学科而言,无可替代的魅力与价值所在吧。
三、一步跨出六百年,古寺新颜话变迁
聆乐学谱,意犹未尽,不觉已近午时。信步走出寺门,三两步上了台阶,一辆汽车从我鼻尖前呼啸而过,一不留神,险些撞上。回头再望,那座幽静的古刹已然融回了禄米仓胡同的日常烟火之中。木漆的神佛、铁铸的车流,几步台阶,清晰地分隔开了百年凝固的沉静与都市奔流的脉搏。
猛然想起这台阶的来历:数百年来,禄米仓胡同的路面因反复修缮而不断抬高,智化寺自乾隆朝王振塑像被毁后,香火渐稀,关注日少。重新修缮后,只得在寺门前砌上这几级台阶,权作与胡同道路的连接。说来也巧,正是这份“无人问津”,反倒使得智化寺在清代三百年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明时的建筑格局与风貌。
想必,1990年寺门重光,看着人流再次熙攘,古刹内的万千佛陀,亦会心生欢喜。只是,当年的人们匍匐于地,敬献香火,是在神佛前安放信仰与敬畏。时光流转,如今的游人则更多地抬头对着壁画彩塑啧啧称奇,将宗教的威严、神秘,品鉴为一种独特的“美学符号”。寺内常驻的乐僧,其职能也从最初的“演乐娱神、诵经礼佛”,转变为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释迦牟尼依旧襟坐莲台,他那穿越六百年的目光,见证了胡同的巨变。此情此景,于我这音乐学子而言,感慨尤深:是庆幸这古乐能以新的方式流传于世,还是惋惜其原始语境的消逝?这个复杂问题难以定论,但这份思考,本身就是收获。
日头已至中天,阳光晃眼,打断了我的万千思绪。再回首,望一眼那深藏于胡同的幽静古刹。从殿宇的恢弘到乐音的苍劲,在这里,中国音乐史变得立体、有声。此次智化寺采风,不仅让同学们亲身领略了“活”的文物与“活”的音乐,更启迪了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在当代如何“活化”与传承的深入思索,因此,这既是一次专业知识的印证,也是一场音乐学人的文化寻根。

采风活动合影
撰稿:梁博睿
摄影、摄像:周泽彤
复核:吴晓萍
签发:何宽钊